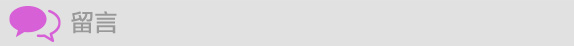思乐女谈:一个90后的“六四”记忆-赵思乐 女权主义媒体人
20160604
东网电视
更多新闻短片

长安街上的鲜血和坦克留给“广场一代”的执念,成了不可磨灭的基因,塑造了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。
作为“90后”,从字面上就能知道,“六四”发生在我出生之前,我没有任何关于“六四”的第一手记忆。在出生后的20多年里,我完全不知道也没有听过“六四”。但对于现在的我,“六四”就像一个熟悉但素未谋面的师友,对我的人生持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,即使我无法准确预测这影响的后果。
第一次听说“六四”,应该是在2011年上半年的南京,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我,为了完成新闻课程的功课,做了关于南京梧桐树被砍伐事件的调查报道,并在微博发表传播。同样关心此事的微博网友找到了我,约我见面,从他口中,我第一次听说“推特”、“翻墙”,也第一次听说“六四”。
现在想来,这个网友应该属于南京的“推特党人”,日常热衷于结识“有潜质”的年轻人,并帮助他们“走出蒙昧”。这似乎是散落各地的“推特党人”都喜欢的活动,一般通过见面吃饭聊天达成,他们把这叫做“饭醉”。
2011年下半年,我到台湾做交换生,有了“肉身翻墙”的便利,才开始系统地从Youtube和图书馆里寻找什么是“六四”。它让我难过,但它仍是一个历史故事,即使我在台湾见过也访问过“八九学潮”的亲历者。
在我这个大陆青年对“六四”感到隔膜的同时,我的台湾学运界朋友们却组成“六四”纪念社团,经营“六四”脸书页,年年组织大型的“六四”纪念活动。“六四”似乎属于他们多过属于我?但我也对同龄的他们也感到隔膜,每次跟他们谈到中国大陆的政治打压和人权问题,他们都只有两种回应方法:真的假的?好夸张哦!
渐渐地,我开始更享受跟台湾四五十岁、经历过党外抗争的人聊天——如果说,跟台湾的社运青年相处时,我像在水底下跟水面上的他们聊天,那么台湾的社运中年们,则是同样有过水面下的生存体验的人——这对我起了奇怪的深远影响,我逐渐发现自己的爱恋对象也锁定了有过“广场”经历的人,在台湾是“野百合学运”,在大陆自然就是“八九学潮”。
经过前面这些铺垫,才能说到下面这件事,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“六四”有着生命的联系的事:
我父母有一本家庭日记本,他们从80年代开始记下家庭中的大事。我认真翻阅过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记录,没有提到“八九”或“六四”,一次都没有。这本日记在那段时间唯一关于公共事件的记录,是1990年9月23日的北京亚运会开幕式,因为,那是我出生的日子。
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第一个参与过“八九学潮”的男友,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,他说:“那真是有史以来最无聊的一届亚运会!”
原因是,“六四”之后社会极为低沉压抑的气氛下,北京市民对亚运会毫无兴趣,亚运会的门票都很难售出,于是北京各高校只好用补贴餐券的方式组织学生去观看比赛。当时的他按着课表去上课,教室却空无一人,他带着疑惑转到图书馆自习。后来才知道,同学是被组织去看亚运足球赛了,因参与“八九”受到审查的他却连通知都没收到。他在亚运会期间就只好苦闷地独自往来宿舍和图书馆。
这个故事给了我一种奇妙的震撼:“哦!原来我的出生跟原来想像的完全不一样。”见过08年奥运会的我,对那个亚运开幕式的想像自然是歌舞升平、激动欢乐的。这种震撼就像重写了我的一小段生命记忆,而要重写的原因仅仅就是“六四”。
后来,我又交往过其他有“广场”经历的人。那段经历,都对他们有着不可忽略也不可逆转的塑造/扭曲:一个“八九一代”,床下一直藏着一个“大声公”,家里、车里、办公室里都有喷漆或简易刀具,好像随时准备着要去革命;另一个“八九一代”,对任何同为“八九一代”的人表现出对当局的幻想和妥协,都忿忿不平、难以接受,他说,坦克都上过街了,有什么理由要民间先妥协;一个“野百合学运”的参与者,他总觉得当年的运动虽然胜利了,他们却没有把胜利的果实保护好,他两岸漂泊,希望中国大陆在转型时不要重蹈覆辙,却越来越失望……
我很快意识到,在这些“广场一代”生命中,有重要的一部分,永远留在了那个广场上。那年那天,长安街上的鲜血和坦克留给他们的执念,成了不可磨灭的基因,塑造了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。
久而久之,我对“六四”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,也有一种特殊的厌恶。参加港台的一些“六四”普及性活动时,我会感到烦躁不安,我真真切切地知道到自己仍活在“六四”的阴影里,不太喜欢别人向我描述那阴影的样子。
我通过亲密关系才能体验“六四”和它的后遗症,这在同龄人中恐怕是难以复制的。年轻人能知道“六四”的就很少,遑论“六四”对自己和社会的影响和塑造。如果问一个有公共关怀的年轻人,是什么影响了他,他可能会提到一些书、一些讲座和一些志愿服务经历,极少会提到“六四”,即使提到也大多是说知道此事时“感到震撼”。
这大概也是“八九一代”的悲哀之处,在市场化洪流和信息垄断之下,他们能提醒自己当年在广场上的同伴“勿忘六四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,更无空间和馀力去为“六四”记忆培养继承人。
在记者张洁平的《占中三步曲》中,发起“雨伞运动”的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:“六四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接触公共领域的门槛,我们绝大部份对政治、社会议题的关心,都是从六四开始的。”另一学联代表锺耀华则说:“每年的五月初,你看一下报章,都会开始讲六四,一直到烛光晚会。我就在想,哇,十几二十万人就去那里坐着?打机不好吗?拍拖不好吗?为什么香港有班人这么执着的?为什么呢?然后就会去找六四是什么,北京发生了什么,香港的反应是什么……对我来说,这就是启蒙。”
对中国年轻一代,这样的启蒙是天方夜谭。
但中国的年轻一代抗争者到底需不需要“六四记忆”?这跟问他们需不需要“文革记忆”、“反右记忆”、“大饥荒记忆”都是类似的,在于他们是否需要再用自己的鲜血去验证专制的性质。并没有一段记忆“必须”有人记住,也没有一群人“必须”守护某段记忆,但就像米兰‧昆德拉说的:“人与极权的斗争,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。”